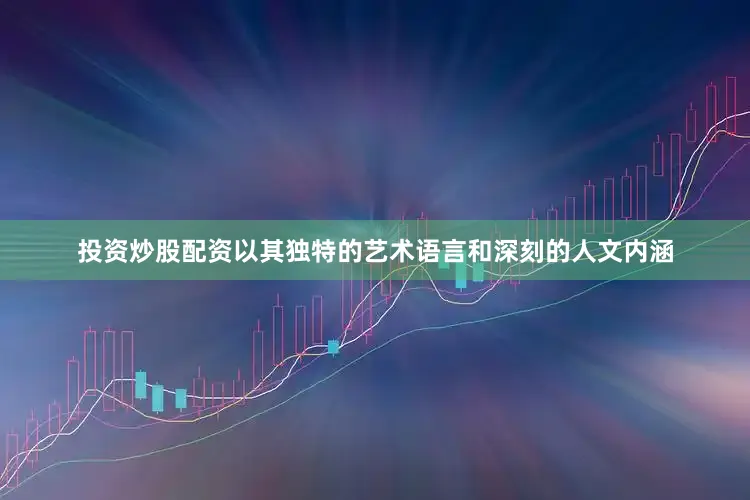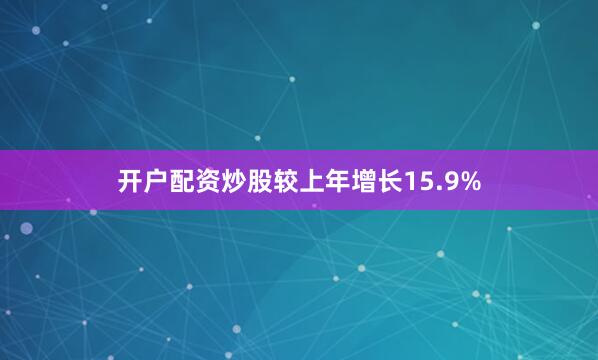当“谪仙人”的名号穿越千年仍在人间回响,我们总会想起那个“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”的李白。
他手握的牌面,是老天偏爱的馈赠——惊世才华震烁古今,上层人脉通达皇室,时代机遇恰逢盛唐崇文之风。
李白手握人人羡慕的好牌,最终却落得“赐金放还”的失意,“流放夜郎”的颠沛,直至在当涂的月色里留下“逐月溺亡”的传说。
究竟是什么,让这位诗仙把人生的一把好牌打得稀烂?

1
李白的第一张王牌,是那足以让天地失色的才华。
《新唐书·文艺传》载他“十岁通诗书,既长,隐岷山”。
这般早慧在神童辈出的史书里屡见不鲜,但李白偏能将天赋淬炼成独一无二的锋芒。
十五岁时,他便在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中写下“十五观奇书,作赋凌相如”的豪言,将西汉辞赋大家司马相如视作追赶的目标,这份少年壮志,岂是常人可及?
开元八年(720年),二十岁的李白离开四川江油,带着一身才学前往渝州拜见刺史李邕。
他笃信自己的才华能让李邕另眼相看,却没有料到,李邕见他举止狂傲,直接就把他拒绝了。
这场碰壁背后,藏着李白无法挣脱的宿命——唐代科举制虽已兴盛,可“刑家之子、工贾殊类不预”的规矩,像一道无形的高墙,将出身工商之家的他挡在了考场之外。
他想走的毛遂自荐之路,在旁人眼中成了急功近利的捷径。
被拒后的李白,挥笔写下《上李邕》一吐胸中块垒:“大鹏一日同风起,扶摇直上九万里。假令风歇时下来,犹能簸却沧溟水。世人见我恒殊调,闻余大言皆冷笑。宣父犹能畏后生,丈夫未可轻年少。”
身居高位的李邕,瞧不上自以为才华横溢的李白,可能有疏漏之处,但是李白直呼其名,也失风度——而且,你既然认为大鹏“同风起”,那又来拜谒李邕干什么呢?
年轻时轻狂,可以理解为热血,自信,有豪情,可是李白一直不改这脾气,吃亏就是难免的了。
李白相信,在重视文人的大唐,自己的才华就是通往仕途的敲门砖,是获取名利的金钥匙。
开元十三年(725年),李白正式出蜀,“仗剑去国,辞亲远游”,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。
他的足迹遍布江南塞北,酒杯里盛满诗朋酒友的情谊,也结识了宰相张说这样的朝中重臣。
可即便如此,他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的理想,依旧遥不可及。开元二十二年(734年),他献上《明堂赋》,以“穹崇明堂,倚天开兮”盛赞开元盛世,也藏着自己渴望被重用的心思。
次年,玄宗李隆基狩猎,他又献上《大猎赋》,特意宣扬道教玄理迎合帝王喜好——可两份倾注心血的辞赋,都石沉大海,没等来诏书的召唤。

2
虽然李白向往的官场没有回响,但在民间收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
于是,李白坚持继续问询河岳,四处游访,所到之处,抱拳的都是名流雅士。
这是李白引以为傲的第二张王牌—— 显赫的人脉。
在湖北安陆,他娶了故宰相许圉师的孙女,这桩婚姻本是他踏入上层社会的绝佳跳板。
以许家的家世资源,可以助李白结识到更多的达官贵人,为他出仕牵线搭桥,再加上李白己经传遍天下的才名,谋个一官半职完全是易如反掌。
但是,可能是天性,也可能是热爱,李白还是纵情山水,流连风物,对亲情视而不见,将为夫为父的责任抛之脑后。
“出门妻子强牵衣,问我西行几日归”。
诗里的眷恋真切,可他还是一次次踏上远游的路,十年婚姻里,实际相处不过六年。
他对家庭的淡漠,让许家人渐渐收回了帮扶的心思。
或许,心高气傲的李白本就不屑于靠许家快婿的身份立足,他要的,是凭自己的名声被世人认可。
转机出现在天宝元年(742年)。
经道士吴筠、玉真公主举荐,再加上太子宾客贺知章的力赞,李白终于迎来了“名动京师”的时刻。
李隆基下诏征他入京。
据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记载,李隆基“降辇步迎,如见绮皓。以七宝床赐食,御手调羹以饭之”——这份“御手调羹”的礼遇,是多少文人一生梦寐以求的荣光!
供奉翰林的李白,只要收敛心性、循规蹈矩,他的官场之路应该是一片光明。
可李白偏不。
杜甫在《饮中八仙歌》里写“李白斗酒诗百篇,长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中仙”。
这看似洒脱的描述,实则藏着他对官场规则的漠视。
“斗酒诗百篇”是才华的馈赠,可“酒家眠”的放浪,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的疏懒,早已越过了朝臣的本分。
更出格的是,他竟借着酒劲,让高力士为自己脱靴,让杨贵妃为自己研墨。
高力士是谁?那是李隆基最宠信的宦官,官至从一品骠骑大将军,皇太子都要称他阿哥,朝臣见了也需礼让三分。
“为朝臣脱靴”本是仆役的活计,李白此举,不仅是羞辱权贵,更是违背了君臣尊卑的大忌。
而让贵妃研墨,即便出于酒后失言,也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折损了皇室颜面。
李白的荒唐远不止于此。
曾有一次,李隆基急召他起草诏书,他却醉得不省人事;平日里,也常因醉酒耽误公务。《旧唐书·李白传》里那句“尝沉醉殿上,引足令高力士脱靴,由是斥去”,道尽了他失宠的必然。
有人说他这是恃才傲物的潇洒,可细想便知,这哪里是潇洒,分明是政治上的幼稚——他既渴望皇帝的赏识,又在得知召见时狂呼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;他既标榜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”,又为杨贵妃写下“云想衣裳花想容,春风拂槛露华浓”的奉承诗句。
这般矛盾的作派,让同僚侧目,也渐渐耗尽了李隆基的信任。
最终,“赐金放还”的旨意传来,他的第一次仕途,以失意收场。

3
李白的第三张王牌,是盛唐的时代机遇,可他终究没有把握住。
李白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,在《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里,他直言要“申管晏之谈,谋帝王之术,奋其智能,愿为辅弼,使寰区大定,海县清一”;“济苍生,安社稷”的抱负,像一团火,始终在他心中燃烧。
可他忘了,盛唐对文学才华的推崇,与对政治才能的要求,本就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。
李隆基欣赏李白的诗才不假,但认为他不具备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也是真。
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中说得很直白:“上素闻其名,召入禁中,既而以为非廊庙器,优诏罢遣之。”
李隆基只是把他当作“倡优”般的文人供奉,从未想过委以重任。
李白的学问庞杂,受道教与纵横家思想影响极深,却缺乏经世致用的系统训练。
同是唐代文人,陆贽以奏议针砭时弊,韩愈以古文革新影响政坛,他们的才学能直接服务于政治实践。
而李白的才华,更多停留在感性的诗歌创作里,即便有谋帝王之术的想法,也终究是纸上谈兵。
如果把第一次仕途失败归咎于性格不合,那么安史之乱中的选择,则彻底暴露了他政治上的弱智。
天宝十四年(755年),战乱爆发,这场浩劫成了文人政治智慧的试金石。
王维被迫任伪职,却以“凝碧池头奏管弦”的诗句表达对唐室的忠诚,乱后得以宽。
杜甫历经千辛万苦也要投奔肃宗李亨,始终站在正统一边,最终成就诗圣之名。
而李白,却做错了选择题。
至德元年(756年),永王李璘奉李隆基之命经营长江流域,三次派人征召李白入幕。
那时的李白,满怀着“为君谈笑静胡沙”的激情,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李璘麾下,还写下《永王东巡歌》十一首,其中“试借君王玉马鞭,指挥戎虏坐琼筵”的诗句,尽显天真。
他全然没有看清时局,这场征召背后藏着皇权争斗的暗流——此时李隆基已退位为太上皇,李亨在灵武自立为帝,李璘手握江南兵权,实则有割据之心。
李白眼中的平叛大业,不过是皇室父子争权的棋子。
当永王李璘被定为叛逆,他也成了附逆之人,最终被判流放夜郎。
虽然后来中途遇赦,可他的人生,早已满目疮痍。
同是身处乱世,早年与李白交好的高适,却走出了一条金光大道。
高适也如杜甫一般,坚定地站在肃宗李亨一边,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讨伐李璘,从寒门子弟一步步做到封疆大吏。
高适的成功,像一面镜子,照出了李白政治判断的盲区——他始终活在自己的理想里,从未真正读懂过官场的规则,也从未看清过时代的棋局。

4
晚年的李白,漂泊无依,生活困顿。
最终,在当涂的某个夜晚,他伴着月色醉酒泛舟,伸手去捞水中的月影,却不慎坠入江中,留下“逐月溺亡”的传说。
这个结局,浪漫得像他的诗,却也透着无尽的悲凉。
有人说,李白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,可若换个角度想,或许正是这份稀烂,成就了永恒的诗仙。
倘若他真的收敛了狂傲,磨平了棱角,在官场上步步高升,史书上只不过会多一个平庸的官僚而已。
人间,却会失去那个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的酒仙,失去那个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诗人,失去那个让盛唐永远鲜活的灵魂。
李白的仕途输了,可他的诗歌赢了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看,李白把仕途的一把好牌打得稀烂,恰恰是中国文化的大幸。
股票配资公司平台,网络配资炒股网站,股票配资股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